“星星的孩子”有个家(附图)
走进梦工场自闭症儿童助长中心
张敬王健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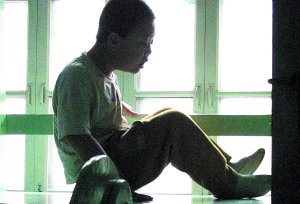
“牛奶、三明治、豆浆、冰淇淋。”老师唱着说出几个词后,让 9岁的彬彬学着唱。
彬彬站了起来,嘴里嘟囔着什么,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。
老师们一边鼓掌一边大声说:“真棒,唱得真好。”
这所奇怪的幼儿园有一个美丽的名字——“梦工场”,它的全称是天津梦工场儿童助长中心。
在这里入托的 13个孩子都是“星星的孩子”——儿童自闭症(孤独症)患者。
他们会忽然怪叫,随便抢别人的东西,一旦学了坏习惯就很难改过来。
他们都不让拥抱,因为他们在拥抱的时候会有痛感。
他们对某些物件,如一只杯子、一块砖表示出特殊兴趣,甚至产生依恋,而对亲人却没有依恋感。
他们对视、听、触、疼痛、冷热等多种感觉迟钝或过敏。正常孩子会被巨大的声音惊吓,而他们却会无动于衷……
患这种病的孩子不能像正常儿童一样与周围的人和环境建立联系,严重缺乏社会适应及交往能力,语言发展有明显障碍或者根本就没有语言,举止刻板……从婴儿期开始出现,一直延续到终身,是一种严重情绪错乱的疾病。
老师们说,孩子们的语言能力很差,但他们却对音乐敏感,一般老师和家长都是把教他们的语言唱出来,这样他们更容易接受。他们能记住那个词已经很了不起了,出不出声并不重要。
“乱”生相

午餐时间到了,每一个“梦工场”里的孩子都需要老师照看,只有一两个孩子可以自己拿勺吃。
6岁的辰辰不爱吃,跑到一边尖叫。
5岁的明明离开座位,一把抢走了强强手里的蛋糕,而强强却没有任何反应。老师赶忙校正明明的行为,告诉他“不可以”,并要求他道歉。
7岁的童童不知什么时候爬到了滑梯顶部,坐在边缘上自顾自地晃动着腿。
8岁的琳琳在老师的引导下说了一声“阿姨好”,可眼睛依然漠视前方。
9岁的牛牛在地上打滚并笑个不停。老师说,只要他兴奋起来就会在地上打滚不起来,见到陌生人还会吐口水。
饭刚刚摆在面前, 12岁的丽丽就哭了起来。老师在旁边温柔地说,“丽丽饿了是吧?不着急啊。”老师把一勺饭喂进丽丽嘴里,“好吃吗?”丽丽摇摇头,低声说:“爱吃鸡蛋黄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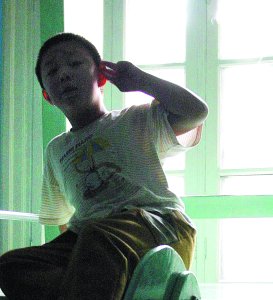
母亲的无奈
患孤独症的孩子中,男孩的比例要远大于女孩。丽丽是“梦工场”里唯一的女孩,也是最大的孩子。她是这些孩子中语言最好的,但是当她饿了的时候,采取的方式仍然是哭。
丽丽的妈妈姓王,是“梦工场”里的老师,负责一些事务性工作。王老师并不避讳谈起自己的女儿,她说,丽丽还有个双胞胎姐姐华华,华华很健康,目前已经上六年级了,而且成绩很好。王老师说,她很对不起华华,为了照顾丽丽,华华从小就随奶奶生活,她几乎把母爱全部给了丽丽。
丽丽是 3岁左右被确诊为孤独症的,当王老师渐渐地明白什么是孤独症后,作为一个母亲,她的心痛到了极点,虽然她还有一个女儿,但她知道丽丽将成为她一生的责任。
“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亲情,可他们最缺乏的就是亲情,他们可能会叫爸爸、妈妈,但根本不了解这两个字后面蕴涵的真正含义,他们可能会跟任何人都叫爸爸、妈妈。”王老师说:“很无奈吧,看上去我们的付出没有回报,但经过训练,孩子在进步,我们就不能放弃,我们要为孩子的未来打造一片天地。”
辍学的孩子
凡是有孤独症孩子的家庭,一般都需要父母中的一个人辞职,专门照看孩子,这样就给家庭造成巨大的经济负担,而且要想让孩子受到专业训练又会有一笔巨大开支,往往一些家庭因为无力支付训练费,孩子长大成人后,就只能关在家里,当他们的父母去世后必将成为社会的负担。
小川就是这样一个孩子,他今年 6岁半了,但还不会说话,偶尔瞬间能发出一两个音,但过两天又不会了。
小川一家住在 10平方米的小屋里,母亲在家照看孩子一直无法出去工作,父亲打工每月挣 800元钱,用来支付一家人的基本生活费用已经捉襟见肘,更不用说送小川参加培训。要命的是小川还有肾病,需要长期服药,小川的父母在家庭现状和孩子的病症的重压下看不到生活的希望。
郭建梅的“梦工场”原本想做成慈善机构免费让孩子们入学,可是,“梦工场”需要场地需要师资,老师们还要定期外出培训,这笔钱从哪儿来?郭建梅本身没有工作,靠丈夫的收入生活,如果“梦工场”完全是公益性的,是根本无法存活的。
为了能让更多的孩子有机会受到专业训练,郭建梅将入学费用降到最低,但还是有的孩子上不起。虽然小川在“梦工场”里的情况有了明显好转,但是无力支付入学费用,不得不重新回到家里,他的情况一下子又回到了从前的混乱状态。像小川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,他们太需要外界的帮助了。
本版撰文新报记者张敬 本版摄影新报记者 王健





